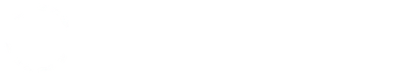心智障碍女性的婚恋困境
浏览:0 日期:2022-05-05
魏来结婚那天是 2020 年 10 月 18 日,她 28 岁。
天气很好,婚礼现场热闹嘈杂,如果不深入交流,人们很难发现新娘是个心智障碍者。由于小时候错误服药,魏来在三岁时被诊断为智力低下、发育迟缓。
心智障碍者,指因不同原因造成智力受损的人群,包括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征、脑瘫造成的发展障碍等。这一群体在中国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根据心智障碍权利倡导机构晓更助残基金会的估算,目前中国的心智障碍者至少有 2000 万人。
如今,《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
法律对心智障碍者的婚姻有了规定,但在更复杂的现实里,他们的婚恋成了理不清的难题。作为女性的心智障碍者,更可能身处双重的弱势情境中。
她们的情感需求是否得到了正视?在婚恋决策中,她们的意愿能否获得认可?社会与家庭给予了她们怎样的支持?走入一段婚姻,她们会面临哪些忧喜,又将面临哪些可能的风险?被忽视的婚恋困境,她们依旧囿于其中。
魏来与丈夫贾海洋的相识,源于同学母亲的介绍。据魏来妈妈所说,那是一个重度自闭症女孩的母亲,她主动表示想给魏来介绍个男朋友。魏来妈妈想:「看看试试吧。」
时间是 2016 年的 5 月,地点约在咖啡店,桌子两边坐着男女双方和各自的父母。
从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来看,两个家庭条件悬殊。这一头,魏来一家祖籍哈尔滨,13 年前来到北京。搬家是因为几乎无处可去,魏来在老家勉强完成了普通小学、中学的义务教育课程。北京拥有相对完善的心智障碍者支持体系,魏来父母工作的国企也有北京分部,商量后,他们在北京买了一套三居室,最终定居在了这座城市。
那一头,贾海洋来自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如今是北京某游泳馆的一名救生员。在魏来妈妈的初次印象中,贾海洋是个脸特别黑的小伙子。来北京前,他在山里帮父母放羊,几十只羊是这个家庭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在北京的住宅是从山上搬来时政府安置的,一共六间宽敞的平房。
贾海洋家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结婚意愿,魏来父母也说:「人品是第一位的,外貌、家庭条件这些,都没有要求。」
中国农业大学学者潘璐曾在河北某县对农村心智障碍女性进行了田野调查,发现她们的婚姻具有「门当户对」的传统特色,但这种对等性主要体现在配偶双方各自的缺陷和劣势上。潘璐观察到,这些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体残疾、存在某种生理缺陷、年龄偏大、家庭经济条件处于社区贫富排序的末端。
魏来不算农村女性,但她的婚姻也体现了「门当户对」的特征。贾海洋来自河北山区,当地女性少于男性,不少女性初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当地男性要想找到合适的同乡女性并不容易。「他们那边娶媳妇,少了也要给六七十万彩礼」,魏来妈妈说。这对于贾海洋的家庭,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
潘璐指出,当这些男性面临婚姻获得危机和传宗接代的家庭压力时,便会将目光转向同样处于劣势的女性,心智障碍女性由此被纳入了他们的选择范围中。这样的结合是「两个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个体的结合」。
而对心智障碍女性的家庭来说,父母老去后,谁来照顾孩子是一个让家长揪心的难题。在这一群体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心智障碍者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比孩子多活一秒钟。」
魏来初中毕业后,在哈尔滨无学可上,又找不到工作,魏来妈妈一度感到无助。查询到北京有好的特教机构,经历了心理斗争后,她决定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原本,她是当地自备水场的水质检测员,放弃做了近 30 年的工作,魏来妈妈坦言,「主要是为了魏来。」
这些年抚养魏来的艰辛,她匆匆带过了,「之前带魏来,学习上是最困难的,别的孩子教一遍就会的,她教千遍万遍也学不会。」她说:「我一直努力想让她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很难,当初这个想法甚至有点是幻想,因为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的。」
想到魏来今后的生活,虽然有托养机构,她从没考虑过将魏来送进去。如今,魏来在一家咖啡馆做服务员,结婚组建了家庭,这让魏来妈妈相信,女儿正在逐渐缩小与普通人的差距。